一个县与国家历史
中国网 china.com.cn 时间: 2010-12-27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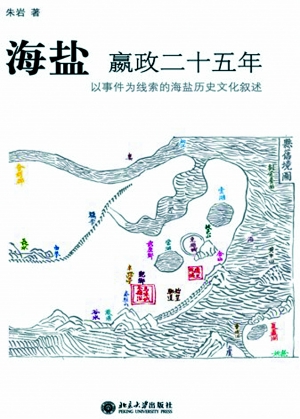
《海盐:嬴政二十五年》 作者:朱岩
□书评人 史远泽
历史,不仅仅是全局性的变动,在诸多碎片与细节的变迁中,往往蕴含了更多激荡人心的故事与想象空间。这是朱岩的《海盐:嬴政二十五年》吸引我的一个原因,另一层原因,我是海宁人,地处海盐之西。浙北区域文化的演变,也让我产生兴趣。
“海盐”是浙江北部一个县,地处长江下游,杭嘉湖平原东端,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故地。与其名相关的是,“海盐”一名的来历,确实与盐有关。春秋战国之际,海盐一带“海滨广斥,盐田相望”。据说在春秋战国之时,就有人“东海煮水为盐”,所以“国富民众”。
“海盐”的历史,从秦王政二十五年(公元前222年)真正开始,这一年,秦国基本削平六国诸国,尤其是长期与秦国争霸的楚国,为秦所灭,原属楚地的版图,并入到秦国的版图之中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秦设会稽郡(以今天苏州为郡治),下设海盐县,这是秦王朝加强对于区域管理的方案,与秦王朝碰上的最大命题相关。秦以一诸侯国,通过百年战争与侵略而有天下,管理国家就成为秦王朝的一大问题,是推行郡县还是重新封建化,对于秦王朝来说,刻不容缓。鉴于封建化诸侯征战不休的历史,秦国选择了更为强硬的中央集权方案,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,会稽与海盐的出现,就是全国郡县制的结果。所以,秦王政二十五年,是海盐的一个开端。
除了建制之外,更大的变化,应该说是文化上的大规模变动,海盐在春秋战国,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,“吴越文化”是海盐的主导文化。秦国在完成建制的统一之后,同样在海盐推行文化的统一,即《史记》所云的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。朱岩在《海盐:嬴政二十五年》中注意到了一个事件,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,路过海盐境内。为此,秦始皇在海盐境内修筑了驰道。所谓驰道,就是当时秦帝国所修筑的国道,因为路面很宽,从施工到修筑,都有一定的标准,主要用来运送战略物资及军事人员。秦驰道,后来为海水所淹,于今日,踪迹难觅。但这一事件本身,却表明了秦帝国合天下为一的雄心。
秦王朝开创了历史,海盐从此纳入到中原王朝的体系之中。尽管中原王朝体系不断变动,但是海盐的位置感没有改变。我指的“位置感”,是指文化心态上的位置感。甚至更为有趣的是,随着中原地区在历史中长期的战乱频仍,少数族裔入侵,中原王朝或崩塌或南迁,江南一带,越来越承担起中国文化中心的任务。这一转变,从两晋开始直到明清,大约花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。《海盐:嬴政二十五年》这本书有趣地叙述了这个变迁的过程,不一样的是,朱岩不是从宏观角度去讲衣冠南渡、南宋的儒学、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繁荣,而是选择了一系列微观事件,同时,这些微观事件,又与当日的国家变动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。于此,我们也可以看出,一个县的起起伏伏,其实是中国命运的起起伏伏。
海盐可以是一个代表,或许,我们选择杭嘉湖区域任何一个县的历史,都能书写出这样一部巧妙的历史。本质上来说,这个区域在行政与文化上的变动,都有一定的同构性。这里,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海宁,海宁县的故事,尤其是其自明清以来文化之繁荣,确实值得大书特书,但这种繁荣,同样也需要摆放进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中来看待。比如科举制下,江南地区往往占得先机,其原因与江南的经济繁荣相关,经济的繁荣建构了一个城市市民阶层,这个阶层的人员热衷于文雅之事,对于出版物,带有天生的热情。与明清江南出版繁荣相呼应的,是藏书读书热,知识被大面积地传播、辩论。从而,作为文化产地的“江南”为中国各地区输出“文化”。江南,逐步成为文化的制造中心,这是历史的逻辑。
往日文化的繁荣,为我们今日研究一个区域的历史,提供了更多材料。这是海盐的事情,这是江南的事情,也是中国的事情。
推荐阅读: